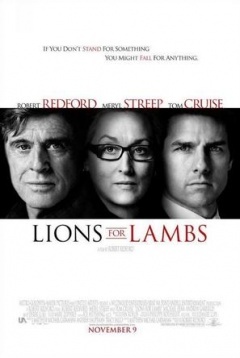- 光线云2
- 光线云1
- 正片
- HD

黎巴嫩
- 主演:
- Reymond Amsalem,奥斯瑞·科恩,Yoav Donat,迈克尔·穆索诺夫,Zohar Shtrauss
- 备注:
- HD
- 类型:
- 战争片 剧情,战争
- 导演:
- 塞缪尔·毛茨
- 年代:
- 2009
- 地区:
- 以色列
- 语言:
- 希伯来语
- 更新:
- 2023-11-06 17:27
- 简介:
- 影片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确切的说,是来自导演本人的生活经历 1982年的一天,黎巴嫩战场上来了四名年轻的坦克兵,他们独自驾驶着一辆坦克驶进了一个平民村庄。这四名年轻的士兵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甚至连驾驶坦克也是刚刚学会的。在这个村庄里,他们的任务是配合地面作战部队清除.....详细
相关战争片
黎巴嫩剧情简介
战争片《黎巴嫩》由Reymond Amsalem,奥斯瑞·科恩,Yoav Donat,迈克尔·穆索诺夫,Zohar Shtrauss主演,2009年以色列地区发行,欢迎点播。
影片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确切的说,是来自导演本人的生活经历 1982年的一天,黎巴嫩战场上来了四名年轻的坦克兵,他们独自驾驶着一辆坦克驶进了一个平民村庄。这四名年轻的士兵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甚至连驾驶坦克也是刚刚学会的。在这个村庄里,他们的任务是配合地面作战部队清除那些看上去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恐怖分子。 他们的指挥官是贾米利,在他的指挥下,这次行动的要点是“快速、简单”。然而当坦克进入村庄那一刻起,这次的任务就不那么简单了。他们和地面部队失去了联系,毫无作战经验的坦克兵们像是无头苍蝇一样乱跑乱撞。一次简单的军事任务也就变成了屠杀。
影片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确切的说,是来自导演本人的生活经历 1982年的一天,黎巴嫩战场上来了四名年轻的坦克兵,他们独自驾驶着一辆坦克驶进了一个平民村庄。这四名年轻的士兵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甚至连驾驶坦克也是刚刚学会的。在这个村庄里,他们的任务是配合地面作战部队清除那些看上去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恐怖分子。 他们的指挥官是贾米利,在他的指挥下,这次行动的要点是“快速、简单”。然而当坦克进入村庄那一刻起,这次的任务就不那么简单了。他们和地面部队失去了联系,毫无作战经验的坦克兵们像是无头苍蝇一样乱跑乱撞。一次简单的军事任务也就变成了屠杀。
黎巴嫩影评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3516.html
大片大片的向日葵,在招展,在开放,在成熟,当世界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再也听不到炮声,再也看不见死亡,再也没有撤退的命令和进攻的指挥,甚至再也没有城区、居民和士兵。可是,在这一望无际的鲜花世界里,在这明亮的白昼时光里,在向日葵中间,却停驻着一辆坦克,一辆架设着炮火的坦克,一辆刚刚冲出包围圈的坦克,一辆即将奔赴下一个战场的坦克。鲜花和坦克,以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组合在那里,是坦克将摧毁着美好的诗意,还是鲜花会消融战火的恐怖?
前者叫突兀,后者叫淹没,前者是破坏,后者是反战。而其实,前者只是停留,后者只是点缀,只有打开坦克顶部的盖子,才能从黑暗的内部世界里走出来,才能看见明亮的光,才能呼吸自由的空气,才能看见盛开的花朵,不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却让人看到光明和希望,看到生命和生长,这是远离战争的美好场景,可是,对于这一架还要执行任务的坦克来说,这不是终点,这不是归宿,远方,以及远方更远处,还有新的任务,还有新的黑暗,还有新的战场,还有新的死亡,只有坦克向前行驶,才是必然的。
必然的道路上,是偶然的经过,必然的战争里,是偶然的诗意,而这种偶然是脆弱的,是哀伤的——只需要一颗炮弹,这一片花海就会被摧毁,就会成为废墟。弱不禁风的美好只不过变成了一种梦幻,而以梦幻开场,以梦幻结束,暂时逃离那硝烟,那战火,那死亡,何尝不是发自内心的呼唤?何尝不是拒绝战争的态度?
1982年,黎巴嫩,在此时此地,只有必然的战争,只有必然的死亡。“犀牛”也好,“灰姑娘”也罢,在被这样一种诗意的名字命名的时空里,它们却指向那冰冷的坦克,指向冷酷的枪炮,指向血淋淋的现实,指向那些被叫做“敌人”的人群。而在这“犀牛”的内部世界里,也只有油腻、黑暗、混乱的空间,它被执行任务,被发射炮火,它的眼前只有被摧毁的废墟,只有被消灭的敌人,只有被击中的目标。作为战争中的存在,它的名字叫做“武器”。而在这个巨大、冰冷、保护自己和屠杀敌人的武器里,被看见的一切也都无法逃脱战争的一切规范。
一个十字准星的瞄准镜,是面向外界的唯一出口,它可以对准敌人,可以瞄准目标,可以发射炮弹,可是,从这唯一的出口里,却也望见了世界存在的一切残酷。那个从街上跑走的小孩,目光是带着愤怒的,那个平静地坐着的老人,目光里是含有仇恨的,而那个失去了丈夫和孩子的女人,目光中更是绝望,是的,他们是活着的人,他们不属于敌人,不属于恐怖分子,不属于打击的目标,但是在他们的眼光里已经看不见希望,他们一视同仁,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恐惧。
而活着的人之外,是那些死去的人,死去的牲畜,一只驴子倒在地上,已经不会挣扎,但是它的嘴还在动,他的眼还在转,对于它来说,奄奄一息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老人的旁边是一个头倒在桌子上人,血模糊了他仅剩的脑壳:那个男人被恐怖分子击中之后,整个身体从楼上掉落下来,重重地摔在地上;还有那些被剥去了皮的动物尸体,还有那些在废墟里再不会起来的无辜平民,甚至还有不断前进而遭到袭击的士兵,也是血淋淋地出现在瞄准镜里。
但是,这瞄准镜绝不是简单观看的窗口,它作为武器一部分,最大的意义是射击。但是谁来射击?他是被执行命令的士兵,他是看见了死亡的战士,他是无法逃避和选择的射击手,“我从没有杀过人。”这是史慕里惊恐的声音,一个没有经历过炮火的新兵,一个没有看见过如此惨烈死亡的战士,面对着手中的发射按钮,他的手是颤抖的,他的心更是恐慌的。看见那些老人无助的目光,看见少年愤怒的目光,那些妇女痛苦的目光,史慕里犹豫过,但是战场的忧郁却可能导致另一场悲剧。当那辆小车驶进他们的视野的时候,起初的命令是用炮火警告,但是在一瞬间前方的伞兵才发现是恐怖分子装扮成平民,再一个命令是开火,但是史慕里犹豫了,就在这犹豫中,敌人的枪声响了,恐怖分子逃离了汽车跑进了香蕉林,失去了机会,却也使得自己人被杀死;而第二次,当前方出现卡车的时候,前方的直接命令是开火,史慕里按下了发射的按钮,却发现那是一辆装鸡的平民卡车,但是打出去的炮弹使得那个可怜的老农失去了脚和手,他在地上痛苦地呻吟,却再也无法站立起来,但是行进的士兵为他补了一枪,死亡,就是这样,从来都是直接而残忍的。因为犹豫而错失了打死敌人的机会,又因为执行命令杀死了无辜平民的死亡,对于史慕里来说,这就是一种战争的煎熬和残酷。而第三次执行任务发射的时候,在瞄准镜里是被恐怖分子劫持的一家人,人质在哀求,敌人在叫嚣,史慕里在命令中又一次经历了挣扎,他在尽可能最小牺牲的情况下开炮,恐怖分子被击毙,而那个幸存的妇女也失去了丈夫和5岁的孩子。
“你以为在过家家?这是战争。”这是坦克“犀牛”里的指挥官阿瑟对他的怒喝,是的,这是战争,这是战场,只有命令,只有射击,犹豫和放弃,从来不是一个军人的职责,但是实际上,如果每一个人走向战争都没有挣扎,都没有怜悯,那人无非是一个工具,而战争的残酷性或者就是要把人当成是工具,泯灭人性,只有你死我活,只有不惜代价,才能最终成为胜利者。但是在这个幽闭、狭窄和黑暗的“犀牛”内部,在这个看上去相对安全和封闭的世界里,射击手、装弹员、驾驶员、指挥官四个人却在这个与外界隔绝的世界里,完成了关于战争的另一种命名,甚至是一种有限的颠覆。
史慕里的犹豫和痛苦,是回归一种人性,他说:“我不想自己的手上沾上他们的血。”而赫泽,这个参加战争时间最长的士兵,却总是抵抗着指挥官阿瑟的命令,他说自己很累,他指责那是“破命令”,甚至他想到了两周之后自己会有度假期。史慕里和赫泽,都在抵抗着命令,都在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而伊高似乎是感情最丰富的一个人,他想起了小时候父亲葬礼上的故事,女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告诉了他这个消息,他抱着女老师,女老师的身体接触到他,让他有了某种冲动,“帐篷式的顶起”使得他不愿离开老师,假装哭泣中抱得更紧,而身体上的摩擦让他体会到了快感,父亲的死本是一件悲伤的事,然而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却是冲动和兴奋,这是一种对死亡的颠覆,最悲伤的情感唤醒了性意识,而这种唤醒和释放却也成为本能的释放,而坦克里的是个人在这样的讲述中,似乎又回归到最为一个人的存在意义。
而伊高在坦克里,也总是惦记着母亲,他希望部队能够通过特殊的方式给母亲报平安,“也许母亲在整理我小时候的照片,她会把照片分成黑白的和彩色的。”对母亲的思念成为最温暖的一幕,似乎也让他们暂时忘记了外面不绝的战火,忘记了随时可能的死亡。而指挥官阿瑟,在那个叙利亚战俘面前,却也处处体现一种人道主义精神,被绑住的战俘总是要尿尿,他拿过那个黑色的盒子,解开他的裤子,然后就蹲在他的身边等他解好。而当他们陷入敌人的包围圈,甚至一度和前方失去联系的时候,阿瑟下达了“向北突围,投入战斗”的命令,而在执行行动之前,他拿出剃胡刀,喷上泡沫,将拉碴的胡子刮干净,因为他说:“不能脏兮兮地上战场。”上战场仿佛是一个仪式,必须体现人的尊严,而他对于战俘的态度同样是一种平等的态度,所以在那个长枪党的人对战俘威胁要挖出一只眼睛割掉鸡鸡的时候,阿瑟却对战俘说:“我们不会杀了你。”
四个人的谈话,四个人的故事,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逃避战争躲避死亡回避痛苦,这是人性的某种回归,而那破碎的玻璃后面的裸体海报,那镜头前废墟上的圣母画像,那被看见图片里的巴黎埃菲尔铁塔、伦敦大本钟、纽约摩天大楼,都像是对于战争的颠覆,对于和平的向往。而那个“犀牛”的铁皮上也印着这样的话:“只有人才是钢铁之躯,坦克不过是一摊金属。”坦克只是冰冷的金属,人才是真正的力量,这就是一种态度,就是一种精神。
但是这个幸福安宁的世界,却是易碎的,坦克外面是随时射击过来的子弹和炮火,是随时可能的死亡,而坦克里面,尽管有故事,有温情,有人性,但是却无法真正逃避,坦克是此次战争的一部分,负责清除障碍、封锁道路,负责打击敌人,掩护部队,而当顶上那个盖子打开的时候,可能会放下来一个死去的士兵,可能会交给他们一个语言不同的战俘,同样是鲜血,同样是死亡,其实和外面的世界相连。行动指挥官贾米尔进入坦克,他便下达了此次行动的两大任务,在他的口里,磷弹必须叫做烟雾弹,俘虏被称为“蟋蟀”,战争是不折不扣执行的命令,也是将一切正常的东西被改写、被命名而纳入其中。而当坦克偏离路线必须离开的时候,每个人都闻到了窒息的味道,因为偏离路线意味着陷入敌人的包围圈,意味着可能遭受打击,也意味着生命的瞬间终结。
已经受损严重的犀牛,在阿瑟下达的“杀出一条血路”的命令中,在伊高惊慌而喊出“我想回家,我想妈妈”的哭泣中,在坦克无法启动众人的恐惧中,终于迎来了最惨烈的打击,强烈的震动和受损让所有人感受到了战争的威力,以及战争的残酷,刚刚接通的对讲信号里传来:已经和家人报平安,是对伊高当初提出的“愚蠢的要求”的回应,可是伊高再也无法听见了,生命变得那么脆弱,一阵颤动,一阵晕眩,一阵黑暗,等恢复过来的时候,伊高已经在鲜血淋淋中死去,他的眼睛却睁着,仿佛在传递着一种无法瞑目的遗憾,像是一个反讽,报平安和死亡,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就像是战争带来的两面,一面是生命,一面是死亡,它们从来不是隔绝在两个世界,就在一瞬间,那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会让鲜活的生变成永远的死。
封闭、逼仄、黑暗、混乱的坦克内部,容纳着小小的人性世界,也走向短短的人生之路,在危机四伏、硝烟弥漫的战场,谁都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开始,又会在什么时候结束,而即使他们在夜晚翻过去之后,在战斗平息之后,在死亡发生之后,迎来了黎明,迎来了光亮,迎来了平静,也迎来了满世界盛开的向日葵,灿烂如此,就像生命应有的样子,绚烂,缤纷,闪耀着成长的力量。但是即使每个人都想要沉醉在这花海中,也只是一个短暂的想象,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下一个任务还在等待着,下一次突围还在准备着,或者,残酷、直接、无从选择的死亡也在前方,而坦克上的那句话已经变成了另一种说法:“没有人是钢铁之躯,他们和坦克一样不过是一摊金属。”
大片大片的向日葵,在招展,在开放,在成熟,当世界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再也听不到炮声,再也看不见死亡,再也没有撤退的命令和进攻的指挥,甚至再也没有城区、居民和士兵。可是,在这一望无际的鲜花世界里,在这明亮的白昼时光里,在向日葵中间,却停驻着一辆坦克,一辆架设着炮火的坦克,一辆刚刚冲出包围圈的坦克,一辆即将奔赴下一个战场的坦克。鲜花和坦克,以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组合在那里,是坦克将摧毁着美好的诗意,还是鲜花会消融战火的恐怖?
前者叫突兀,后者叫淹没,前者是破坏,后者是反战。而其实,前者只是停留,后者只是点缀,只有打开坦克顶部的盖子,才能从黑暗的内部世界里走出来,才能看见明亮的光,才能呼吸自由的空气,才能看见盛开的花朵,不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却让人看到光明和希望,看到生命和生长,这是远离战争的美好场景,可是,对于这一架还要执行任务的坦克来说,这不是终点,这不是归宿,远方,以及远方更远处,还有新的任务,还有新的黑暗,还有新的战场,还有新的死亡,只有坦克向前行驶,才是必然的。
必然的道路上,是偶然的经过,必然的战争里,是偶然的诗意,而这种偶然是脆弱的,是哀伤的——只需要一颗炮弹,这一片花海就会被摧毁,就会成为废墟。弱不禁风的美好只不过变成了一种梦幻,而以梦幻开场,以梦幻结束,暂时逃离那硝烟,那战火,那死亡,何尝不是发自内心的呼唤?何尝不是拒绝战争的态度?
1982年,黎巴嫩,在此时此地,只有必然的战争,只有必然的死亡。“犀牛”也好,“灰姑娘”也罢,在被这样一种诗意的名字命名的时空里,它们却指向那冰冷的坦克,指向冷酷的枪炮,指向血淋淋的现实,指向那些被叫做“敌人”的人群。而在这“犀牛”的内部世界里,也只有油腻、黑暗、混乱的空间,它被执行任务,被发射炮火,它的眼前只有被摧毁的废墟,只有被消灭的敌人,只有被击中的目标。作为战争中的存在,它的名字叫做“武器”。而在这个巨大、冰冷、保护自己和屠杀敌人的武器里,被看见的一切也都无法逃脱战争的一切规范。
一个十字准星的瞄准镜,是面向外界的唯一出口,它可以对准敌人,可以瞄准目标,可以发射炮弹,可是,从这唯一的出口里,却也望见了世界存在的一切残酷。那个从街上跑走的小孩,目光是带着愤怒的,那个平静地坐着的老人,目光里是含有仇恨的,而那个失去了丈夫和孩子的女人,目光中更是绝望,是的,他们是活着的人,他们不属于敌人,不属于恐怖分子,不属于打击的目标,但是在他们的眼光里已经看不见希望,他们一视同仁,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恐惧。
而活着的人之外,是那些死去的人,死去的牲畜,一只驴子倒在地上,已经不会挣扎,但是它的嘴还在动,他的眼还在转,对于它来说,奄奄一息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老人的旁边是一个头倒在桌子上人,血模糊了他仅剩的脑壳:那个男人被恐怖分子击中之后,整个身体从楼上掉落下来,重重地摔在地上;还有那些被剥去了皮的动物尸体,还有那些在废墟里再不会起来的无辜平民,甚至还有不断前进而遭到袭击的士兵,也是血淋淋地出现在瞄准镜里。
但是,这瞄准镜绝不是简单观看的窗口,它作为武器一部分,最大的意义是射击。但是谁来射击?他是被执行命令的士兵,他是看见了死亡的战士,他是无法逃避和选择的射击手,“我从没有杀过人。”这是史慕里惊恐的声音,一个没有经历过炮火的新兵,一个没有看见过如此惨烈死亡的战士,面对着手中的发射按钮,他的手是颤抖的,他的心更是恐慌的。看见那些老人无助的目光,看见少年愤怒的目光,那些妇女痛苦的目光,史慕里犹豫过,但是战场的忧郁却可能导致另一场悲剧。当那辆小车驶进他们的视野的时候,起初的命令是用炮火警告,但是在一瞬间前方的伞兵才发现是恐怖分子装扮成平民,再一个命令是开火,但是史慕里犹豫了,就在这犹豫中,敌人的枪声响了,恐怖分子逃离了汽车跑进了香蕉林,失去了机会,却也使得自己人被杀死;而第二次,当前方出现卡车的时候,前方的直接命令是开火,史慕里按下了发射的按钮,却发现那是一辆装鸡的平民卡车,但是打出去的炮弹使得那个可怜的老农失去了脚和手,他在地上痛苦地呻吟,却再也无法站立起来,但是行进的士兵为他补了一枪,死亡,就是这样,从来都是直接而残忍的。因为犹豫而错失了打死敌人的机会,又因为执行命令杀死了无辜平民的死亡,对于史慕里来说,这就是一种战争的煎熬和残酷。而第三次执行任务发射的时候,在瞄准镜里是被恐怖分子劫持的一家人,人质在哀求,敌人在叫嚣,史慕里在命令中又一次经历了挣扎,他在尽可能最小牺牲的情况下开炮,恐怖分子被击毙,而那个幸存的妇女也失去了丈夫和5岁的孩子。
“你以为在过家家?这是战争。”这是坦克“犀牛”里的指挥官阿瑟对他的怒喝,是的,这是战争,这是战场,只有命令,只有射击,犹豫和放弃,从来不是一个军人的职责,但是实际上,如果每一个人走向战争都没有挣扎,都没有怜悯,那人无非是一个工具,而战争的残酷性或者就是要把人当成是工具,泯灭人性,只有你死我活,只有不惜代价,才能最终成为胜利者。但是在这个幽闭、狭窄和黑暗的“犀牛”内部,在这个看上去相对安全和封闭的世界里,射击手、装弹员、驾驶员、指挥官四个人却在这个与外界隔绝的世界里,完成了关于战争的另一种命名,甚至是一种有限的颠覆。
史慕里的犹豫和痛苦,是回归一种人性,他说:“我不想自己的手上沾上他们的血。”而赫泽,这个参加战争时间最长的士兵,却总是抵抗着指挥官阿瑟的命令,他说自己很累,他指责那是“破命令”,甚至他想到了两周之后自己会有度假期。史慕里和赫泽,都在抵抗着命令,都在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而伊高似乎是感情最丰富的一个人,他想起了小时候父亲葬礼上的故事,女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告诉了他这个消息,他抱着女老师,女老师的身体接触到他,让他有了某种冲动,“帐篷式的顶起”使得他不愿离开老师,假装哭泣中抱得更紧,而身体上的摩擦让他体会到了快感,父亲的死本是一件悲伤的事,然而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却是冲动和兴奋,这是一种对死亡的颠覆,最悲伤的情感唤醒了性意识,而这种唤醒和释放却也成为本能的释放,而坦克里的是个人在这样的讲述中,似乎又回归到最为一个人的存在意义。
而伊高在坦克里,也总是惦记着母亲,他希望部队能够通过特殊的方式给母亲报平安,“也许母亲在整理我小时候的照片,她会把照片分成黑白的和彩色的。”对母亲的思念成为最温暖的一幕,似乎也让他们暂时忘记了外面不绝的战火,忘记了随时可能的死亡。而指挥官阿瑟,在那个叙利亚战俘面前,却也处处体现一种人道主义精神,被绑住的战俘总是要尿尿,他拿过那个黑色的盒子,解开他的裤子,然后就蹲在他的身边等他解好。而当他们陷入敌人的包围圈,甚至一度和前方失去联系的时候,阿瑟下达了“向北突围,投入战斗”的命令,而在执行行动之前,他拿出剃胡刀,喷上泡沫,将拉碴的胡子刮干净,因为他说:“不能脏兮兮地上战场。”上战场仿佛是一个仪式,必须体现人的尊严,而他对于战俘的态度同样是一种平等的态度,所以在那个长枪党的人对战俘威胁要挖出一只眼睛割掉鸡鸡的时候,阿瑟却对战俘说:“我们不会杀了你。”
四个人的谈话,四个人的故事,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逃避战争躲避死亡回避痛苦,这是人性的某种回归,而那破碎的玻璃后面的裸体海报,那镜头前废墟上的圣母画像,那被看见图片里的巴黎埃菲尔铁塔、伦敦大本钟、纽约摩天大楼,都像是对于战争的颠覆,对于和平的向往。而那个“犀牛”的铁皮上也印着这样的话:“只有人才是钢铁之躯,坦克不过是一摊金属。”坦克只是冰冷的金属,人才是真正的力量,这就是一种态度,就是一种精神。
但是这个幸福安宁的世界,却是易碎的,坦克外面是随时射击过来的子弹和炮火,是随时可能的死亡,而坦克里面,尽管有故事,有温情,有人性,但是却无法真正逃避,坦克是此次战争的一部分,负责清除障碍、封锁道路,负责打击敌人,掩护部队,而当顶上那个盖子打开的时候,可能会放下来一个死去的士兵,可能会交给他们一个语言不同的战俘,同样是鲜血,同样是死亡,其实和外面的世界相连。行动指挥官贾米尔进入坦克,他便下达了此次行动的两大任务,在他的口里,磷弹必须叫做烟雾弹,俘虏被称为“蟋蟀”,战争是不折不扣执行的命令,也是将一切正常的东西被改写、被命名而纳入其中。而当坦克偏离路线必须离开的时候,每个人都闻到了窒息的味道,因为偏离路线意味着陷入敌人的包围圈,意味着可能遭受打击,也意味着生命的瞬间终结。
已经受损严重的犀牛,在阿瑟下达的“杀出一条血路”的命令中,在伊高惊慌而喊出“我想回家,我想妈妈”的哭泣中,在坦克无法启动众人的恐惧中,终于迎来了最惨烈的打击,强烈的震动和受损让所有人感受到了战争的威力,以及战争的残酷,刚刚接通的对讲信号里传来:已经和家人报平安,是对伊高当初提出的“愚蠢的要求”的回应,可是伊高再也无法听见了,生命变得那么脆弱,一阵颤动,一阵晕眩,一阵黑暗,等恢复过来的时候,伊高已经在鲜血淋淋中死去,他的眼睛却睁着,仿佛在传递着一种无法瞑目的遗憾,像是一个反讽,报平安和死亡,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就像是战争带来的两面,一面是生命,一面是死亡,它们从来不是隔绝在两个世界,就在一瞬间,那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会让鲜活的生变成永远的死。
封闭、逼仄、黑暗、混乱的坦克内部,容纳着小小的人性世界,也走向短短的人生之路,在危机四伏、硝烟弥漫的战场,谁都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开始,又会在什么时候结束,而即使他们在夜晚翻过去之后,在战斗平息之后,在死亡发生之后,迎来了黎明,迎来了光亮,迎来了平静,也迎来了满世界盛开的向日葵,灿烂如此,就像生命应有的样子,绚烂,缤纷,闪耀着成长的力量。但是即使每个人都想要沉醉在这花海中,也只是一个短暂的想象,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下一个任务还在等待着,下一次突围还在准备着,或者,残酷、直接、无从选择的死亡也在前方,而坦克上的那句话已经变成了另一种说法:“没有人是钢铁之躯,他们和坦克一样不过是一摊金属。”